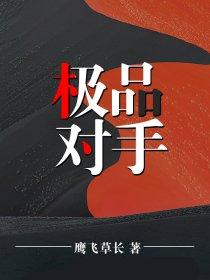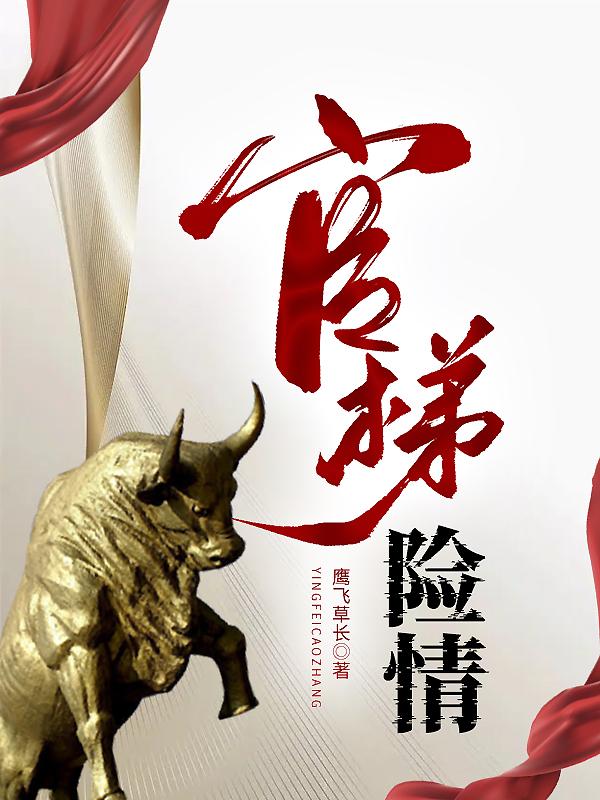书文小说>出家后,在路上捡到忠犬杀手 > 第56章(第1页)
第56章(第1页)
“我岂是这种人,在下都是一视同仁的。”刘紫苏一阵心虚,实际上,被这姑娘猜对了,自己还真就是专门宰那些有钱人的。
“我给你两万两,剩下一万两,就义诊帮,那些没钱治病的人吧。”
刘紫苏拱手说道:“姑娘大义之人啊。”
“毕竟,这些钱我一年就赚回来了。”
三人来到刘紫苏住的小院中。院子里地种满了各种药草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药香气,还有只大黄狗,看样子是专门养来看这些药草的。因为谢月凌看到一朵绿色的花,好奇的想去摸摸,就被小狗警告了。
刘紫苏端来两碗热腾腾的粥递给谢月凌二人,还有几碟子小菜,看样子就是很穷。
“说起来,我有个疑问。”谢月凌接过碗,问道,“神医谷,怎么看着不像神医谷,还有,你一个神医,怎么会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?而且,看你平时的样子,完全不像大夫,倒更像……”她顿了顿,指了指外面的农田,“像个农夫。”
刘紫苏笑了笑,“庸俗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,不一定非要穿金戴银、住在高楼广厦里。这里安静,能让专心研习医术,还能顺便种种地,挺好的。”
接下来的两年时光,谢月凌和村长商量,在药王谷购置了一处小房子,与昕寒安稳地住了下来。
每日,她按时服用刘紫苏配的药,隔几日,便去刘紫苏处针灸。
日复一日的调养中,谢月凌也觉的自己的身体逐渐好转了,不再像从前那般虚弱,心悸,每至秋冬便卧病在床,情绪激动便头晕了。
在这期间,谢月凌也对药王谷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。原来真正的神医谷隐匿在更深处的山上,有位医术超凡的神医在此隐居,轻易不见外人,只有在下山义诊之时,会挑选一些有资质的弟子带入山中,传授医术。
学有所成的弟子,有的选择下山,悬壶济世,像虞大夫、刘紫苏便是如此;而有的则留在山中,传承衣钵,让医谷的医术得以代代相传。
在村子里住的久了,谢月凌越来越觉得这里的民风淳朴,非常宜居。刚搬进新家时,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,连米缸都是空的,村民们见他们这对“小夫妻”生活不便,纷纷自发地送来粮食。
谢月凌向来习惯用钱财答谢他人=,这次也不例外,她刚要掏出铜板,村民们却纷纷摆手,满脸笑意地说道:“哎呀,这小夫妻不懂过日子嘞,这点蔬菜都是自家地里种的,不值啥钱。”
无奈之下,他们只好下山采购的时候,在集市多买些肉、点心和布料,挨家挨户地分送给村民们,毕竟还得在村子里住上好些日子,得打好关系不是。
起初还有人推辞,但谢月凌笑说,以后要是再拿婶子的菜,自己也不好意思了,这他们才收下,嘴里不停地说着要啥来家拿的话。
谢月凌从来没想过,自己有一天也当上夫子了。一日,她如往常一样在自家院子里看书。来了几个小孩子,叽叽喳喳的问书上的东西是什么,谢月凌才发现,这群孩子竟然都不认字。
一番打听后得知,学堂都远在镇上,这偏远的山里根本没有夫子前来授课。这里的村民们生活本就不富裕,也拿不出多余的钱财送孩子去镇上的学堂读书。大家原本也想凑钱请个夫子来山里教书,可凑不出足够的束脩,孩子们便只能一直当“睁眼瞎”。
不过谢月凌平日里看的大多是道家典籍,在文学启蒙方面虽不算精通,但识字教学还是绰绰有余的。
于是,她去集市上买了些《三字经》教孩子学字,学完《三字经》,接着便是《千字文》,之后还有《论语》……谢月凌便这样教着他们,反正自己带了不少钱,不如花了算了,带回去怪麻烦的。按师父的话,积德行善不是。
村里的村民们见谢月凌热心地教孩子识字,纷纷不留自家孩子在家干活了,而是将孩子送来读书,还带来了自家种的麦子、新鲜的蔬菜,当作给谢月凌的束脩
一时间,谢月凌家中的粮食堆得越来越多,几乎都快堆不下了。谢月凌和昕寒两人根本吃不完,所以她特意在村里请了一位手艺好的大娘,把粮食煮了,留学生在家里吃中午饭。
有些孩子实在闹腾,坐在书桌前没一会儿就开始坐立不安。谢月凌看着他们那副模样,不禁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学堂的调皮模样。
要是让祭酒见她如今竟然在教孩子学问,,怕是得气得脸一阵青一阵白,然后又会笑骂她不可贪玩,以免误人子弟。
所谓是“有教无类”,谢月凌就让那些闹腾的孩子和昕寒学些防身的武术,孩子们一听,顿时来了精神。
谢月凌见状,和他们定下规矩:只有学完规定的字,才可以去学功夫,不然就全部让爹娘拎回家,吃“竹子炒肉”。
读书识字至关重要,虽然谢月凌并不喜欢读书,但也明白读书的好处。
多识几个字,总比不识字强得多,若是将来有机会出门闯荡,即便迷路了,只要能写出镇子的名字,也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也不会因为不识字,稀里糊涂地签了契,被人骗得倾家荡产。
第72章宜嫁娶
村门口,暖阳如纱,谢月凌惬意地靠在村口那棵枝老槐树下,手里捧着一把瓜子,悠哉游哉地嗑着,再和婶子聊聊天,眼睛时不时瞟着远处,做颗望夫石。
如今的昕寒,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充实,不再像从前那般奔波于江湖,接各种悬赏令,而是当起了一名猎手。